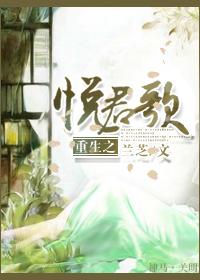龙腾小说网>锁定红海 > 第8部分(第2页)
第8部分(第2页)
《硕鼠》起初引起我的注意在于其中的“三岁”。我在《向东》一书中已经解释过,此“三岁”可能为古代“一番”,就是从红海到中国内地之间的一个来回的航海时间,相对固定,一般不超过“三年”。与其对应的是,《圣经》记载所罗门派大船队出去搜寻珍宝来回一次的时间也是三年一次。后来看陆地行程一个来回也不超过“三年”。清朝锡伯族人从中国东北调遣至新疆伊犁、喀什戍边,单向行程大约使用了一年三个月,人员约4000。从以色列到中国西北地区距离相差并不太远,“三年来回”说法也基本成立。
“三岁贯女”就是中东殖民统治者“三年”来收取一次贡纳。此诗尽管埋怨三年一期的被迫贡纳,但这个诗人未必明白三年一次的贡纳是交给谁的,或许他认为那些直接的收集人就是受惠者,所以他的愤怒是直接冲他们的,或许他明白真正的受惠人实际上也不影响埋怨吧。在悲愤之中诗人明确地表达了另外的情绪,实际上许多《诗经》作品都表达了另外一种情绪:思乡。类似的诗歌很多,但以往中国学者都把那些近乎绝望的思乡情绪解释为思念中国的某地。另外,我认为这些诗歌的作者多为贵族,他们思念远在中东的家乡,所以绝望而无奈。
在这里我有一个推测,中国的“三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未必是同族同种,很可能统治者是新贵,而被统治者多为已经本土化的旧人,所以在考古方面会得出一些结论,整体看现在的考古发现此时人种已多为所谓的蒙古人种,而那些欧罗巴人种或者尼格罗人种相对罕见。这个概率上的结果会导致更多的误解,直接导致了“中国文明独立说”大行天下,实际上所谓文明的传播者主要看那些上层的统治者而不是被统治者。这从几百年前欧洲殖民者在太平洋岛或者美洲的殖民过程就可以看出。
《硕鼠》表达了诗人的愤恨,最重要的是说出了理想:离开你这可恨的地方,我要到那迷人的“乐土”去。导入“西方乐土”,则诗人的理想实际上在“西方”也。所以此诗是一首怀念“西方”的思乡曲。
逝将去女,
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
爰得我所。
逝将去女,
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
爰得我直。
逝将去女,
适彼乐郊。
乐郊乐郊,
谁之永号!
我一定会离开你到“乐土”去,“乐土”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到了那个“幸福的地方”再无话说。请注意三段共同使用了一个“乐”字来形容那个令人神往的地方,那个地方无论怎样形容都离不开“乐”这个美妙的特征。实际上,“乐土”、“乐国”、“乐郊”就是同一个地区的三种不同叫法而已。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寻找“乐土”(2)
那么中国《诗经》中的“乐土”到底在哪里?
“乐土”可能就是今天也门国附近的红海地区!
也门在古代的别名就叫“幸福之地”,或者也有翻译为“天堂福地”、“阿拉伯的乐园”(Arabia Felix)、“绿色也门”等。古代的“seba”其中一个含义就是“通往天堂的大门”。 “天堂”应该就是“乐土”,“天堂”就是“伊甸园”,“乐土”就是“伊甸园”。
txt小说上传分享
“乐土”与“伊甸园”
也门濒临的“亚丁湾”因为古代与中国之间的频繁海上商业联系曾经被称为“中国走廊”等,可见两地曾经有过的紧密联系达到何样一个程度。中国《诗经》的“乐土”所指为“幸福之地”的“也门”决非无稽之谈。中国考古界现在要弄明白的不是两地3000年前是否有海路商业联系,而是这一海上往来起于何年,是3000年前、5000年前、6000年前,还是7000年前?这一点非常关键,它会解开中国东部包括“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的真正起源,它们应该都属于典型的海洋文明。
由于“亚丁湾”(英文名字)叫“Gulf of Aden”,有西方人推测这里就是古代苏美尔语中的“亚底诺”或“天堂”,也就是所谓的“伊甸园”(Eden)。
“伊甸园”本意是“人间乐园”、“幸福之地”。故而,我认为2600年前中国《诗经》之《硕鼠》所表达的“乐土”不仅指也门国土,也暗示我们:也门这里的“亚丁湾”就是“伊甸园”的一部分,《圣经》所谓“伊甸园”与也门相距不远。假如我特别大胆一些的话,我甚至可以猜测“也门”就是“伊之门”、“伊甸园之门”。既然也门地区在3000多年前曾经与中国嫌疑使用同一种语言,那么他们一定有一些相通的语音遗留下来,我们直接把“yemen”这个发音转化为我们熟悉的汉语就可以了。这很简单,但需要脑筋急转弯。不过,我们还是运用传统谨慎的思维继续前进吧。
乐郊乐郊,
谁之永号!
是啊,回到“伊甸园”,谁还会有遗恨!
通过比较从“Eden”(伊甸园)与“Aden”(也门的亚丁湾)的读音,可以发现它们非常相像,分别只在第一个元音,而这一差别很有可能是当初以拼音文字命名时人为误差造成的。要知道,语言出现可能已有上万年的历史,拼音文字的出现也不过是在几千年前,“E”与“A”的差别只是个“落实”为文字时出现的问题。想想粤语与普通话的巨大差别,或许就可以“谅解”这一差别了。
在古代,阿拉伯半岛或者阿拉伯某些特殊城市一直被中国人意译为“天方”、“天房”,它们也蕴涵着“人间天堂”的含义,与音译的“伊甸园”同义:天堂。“房”者,“堂”也。“天房”即为“天堂”,“乐土”就是“伊甸园”。红海东岸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可能都是“伊甸园”。###文化似乎更倾向于“天堂”就在红海东岸这里。或许,正是因袭了这个文化,我们的祖先在《诗经》中正是把“乐土”也定位于红海东岸这同一个地方了?
这里我也指出另外一个嫌疑,“迦南”(Canaan)在俗语中也有“所向往之地”、“天国”、“乐土”的含义。假如说同有“乐土”称呼的亚丁湾两岸与地中海东岸的迦南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分别在红海的两端,另外,他们同属于闪含人聚集的地区。有关“迦南”的分析将在我的下一本书中进行讨论,本书集中于红海南端的“乐土”。不过可以预先告知的一个线索是,部分红海南端的人们,比如一些索马里人就认为他们是腓尼基人后裔,而腓尼基人实际上属于迦南人。
关注人类起源(1)
我越来越觉得,假如我要关注文明的起源,似乎也要稍微关注一下人类起源才更全面,尽管两者并不是同一概念,但他们之间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关于人类起源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多地区起源,一种是非洲单一起源。自从DNA技术参与以来,“非洲单一说”占了上风,这使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学者十分难堪,中国人的DNA与世界各地区的DNA从目前的实验室结论看只有非洲老祖母的痕迹,没有其他祖源,并且时间已经推进到十几万年前。起码目前的情况如此。我们可以等待更多的研究结论。其实我个人很怀疑其他地区也零星有些起源的,只是他们人数过于稀少,尚未构成规模,或者说独立文明还没有出现就受到了冲击。但即便其他地区有人类的起源,也不影响我的结论,毕竟我是研究文明起源的,我关注的核心是最近一两万年的文明成因与流向。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接受DNA技术之下的中国人“来自非洲”的结论,但比较奇怪的是他们依然不接受中国文明来自非洲那个方向。有人认为在中国与中东同时发展了文明,甚至早于中东发展出文明。当然这并非没有可能,但是概率不大。仅只从逻辑上讲,假如按照“夏娃理论”(即人类只有一个非洲源头,并且大致起始于十几万年前)从非洲出来的人类一直向四面八方扩散。由于他们没有发达的组织纪律,也没有国家、民族概念,那么这个自由迁徙的态势就应该一直存在。什么时候这个状态才会停止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最为关键。它将触击文明产生的的源流问题。比如我自己认为人类一直相对自由迁徙,第一次在中国方面的受阻我设定为中国人认为的夏王朝的起源时间,即大约4000年前。但真正的形成严重的致命阻隔应该是在东周时期。所以,在这个模式下中国的夏商周应该有浓重的外来色彩,或者说有外来的极大可能。
强调中国文明独立说的人通常把现代人迁徙的中断表述为大约2万年前。我认为他们这样推测不符合逻辑,因为假如人类一直在全球自由迁徙的话,他们为什么在2万年前突然改变方向不能得到圆满解释。在这个时间里,全球气候或地理只因为第四次冰期的结束而变得方便,而不是不方便,所以把人类迁徙假设为在2万年前突然停止迁徙就显得没有道理。但是假如不让人类在2万或1万年前停止向中国走来,势必中国的文明起源就不能纯洁。
彻底否定DNA的猜测,根本不承认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
相邻推荐:目睹殡仪馆之诡异事件 你种田来我种田 穿越路西菲尔 魅影魔都 琉璃时代 恶邻靠边闪 东邦-可怜房东 家有霸妻 图腾火麒麟 双重生,四爷福晋不好惹 碧蛇相公,萌萌哒! 虎妖 秦思传 很想很想你(完) 都市神仙 翻天小山神 古武仙路 一只吸血鬼的职业生涯 民国那些人 血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