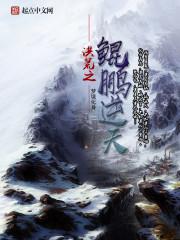龙腾小说网>印度三部曲3:百万叛变的今天 > 第四章 小型战争(第1页)
第四章 小型战争(第1页)
此城名谓迈拉波,
美丽雄伟又富庶;
古来异端拜偶像,
至今仍然未悔改。
——卡蒙斯《路济塔尼亚人之歌》(1572)
一九六二年八月某天,在喜马拉雅山脉某处,我正随着一年一度的朝圣人潮前往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阿马尔纳特山洞,去参拜洞中由冰柱形成的“林伽”——湿婆的象征。那时候,我遇到了“蜜糖”。他来自南方的马德拉斯,身材有点魁梧,相貌柔和。我们成了朋友。两个多月后我到了马德拉斯,又跟他见了几次面。他是个婆罗门,住在名叫迈拉波的婆罗门地区,就在那座著名古庙①附近。他是个忧郁内向的人:他在喜马拉雅山上看来如此,回到马德拉斯自家周边看来还是如此。他话很少。他不吝惜的是没有条件的友谊,全心全意投入、看不出有什么保留的友谊。他总是随时都可以见朋友,随时都乐于见朋友。他将近四十岁,但尚未结婚。他跟双亲住在迈拉波一栋舒适的中产阶级住宅里。
那回我在印度待了一整年。抵达印度数周后我便北往克什米尔,在那边做了几个月的工作,然后赴南方旅行。在乡下,我有时会跟结识的年轻政府官员待在一起,有时则投宿公家机关的小屋及招待所——这些是只提供最基本设备的简单房舍,虽然在绿色革命②之前的印度乡下,那种设备算得上奢侈。
在城市里,我到付得起费的旅馆投宿。未到印度之前,我原以为那边劳动力既然那么多,旅馆应该既好又便宜,就像五十年代早期的西班牙旅馆那样。事实不然。当时,印度几乎没有观光业,酒店管理也还不是一门专业。在小城经营小旅馆的人只能提供跟他们自己所使用的相同的设备,他们雇用的工作人员就像是他们自己家里那些衣衫褴褛的仆人。
马德拉斯的情形却不一样。供应素食的餐厅和旅馆都干干净净的(虽然顾客较多的荤食店或被古怪地称为“军用”的店家,跟北方的一样糟)。干净和吃素是有关联的,二者都是南方婆罗门宗教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在林地大饭店,我住的是增建部分中一个干净的房间,到有冷气的餐厅用餐,坐在大理石桌前取来盛在香蕉叶上的食物(使用香蕉叶是为了洁净,也为了发思古之幽情)。饭店屋外有花园及一座露天剧场或舞台。
如果我先前对南方的婆罗门印度教文化一无所知,如果我对婆罗门成就卓越的音乐和舞蹈艺术一无所知,那么我一到南方,就应该开始对那种文化有点概念了:我看得出,在这里,种姓——犹如伊丽莎白时代的“等级”观念——发挥着抑制文化、社会和身体上的各种混乱的作用,而这些混乱在印度是很容易发生的。
但是,在认识到这文化所扮演的防护作用的同时却也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在林地大饭店的餐厅接触到南方的素食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这完全不像我从小就设想为印度基本食物的那种素食,譬如木豆和无酵素面包等。为林地大饭店招徕不少顾客的这种南方素食过分精致和清淡,我吃进肚里毫无感觉,从未觉得吃饱过。
宗教和食物一样奇怪。蜜糖要我去看看迈拉波的寺庙,他一向在那里拜神。可是,我在特立尼达成长时所认识的印度教几乎完全不涉及寺庙。我知道礼拜仪式是怎么一回事,它们是在家里举行的。我那位在印度出生的祖父于二十年代在特立尼达盖了一栋房子,就在房子最顶端设了间礼拜室。我最熟稔的是不时举行的史诗及经文念诵仪式。信徒隔着一个特别制作、加上装饰的陶质神龛与长老相对,神龛上摆着一盏圣火,燃烧的含树脂油松发出一股香甜的味道。念诵中,每隔一段时间,有人会把净化奶油和糖加进火里,然后摇铃,敲铜锣,有时还会吹海螺。文字的念诵,以及一旁伴随的缓慢有规律的音乐:这是我成长时所接触到的印度教,而这就足够让我感到莫测高深了。蜜糖想让我认识的关于寺庙的种种——关于神圣场所、寺庙里特别供奉的主神等等——实在令我摸不着边,甚至让我有点乱了思绪。
虽然马德拉斯让访客宾至如归,我在那里却一直有置身异域的感觉。雕刻的金字形庙塔;棕榈树;光着上身在旧石柱间出入的婆罗门;迈拉波那座巨大美丽的贮水池,池内四周都设有石阶:这些就像是昔日欧洲旧版画插图中的景物。特别是那些庙塔,它们一再让我感受到视觉上的小震撼,每次都觉得我又在以新的眼光看着那地方;觉得当地的文化依然完整;觉得我所见到的跟最早的旅游者收入眼底的没什么不同。
旅游者,海洋:每当想到马德拉斯,我总会同时回忆起黎明时刻散步到那城市又长又宽的海滩上去的情景。日出时,人们在海里清洗他们养的牛。太阳从海面上升起;平坦的湿沙滩闪着红黄两色;肋骨清晰可见、臀部骨瘦如柴的带角的牛站在它们模糊的倒影上;然后白昼的炙热开始降临。
不到五年之后,我又来到马德拉斯待了几天。当时刚举行过邦议员选举(我倒不是为此而来),我抵达那天,林地大饭店里的气氛就像是殖民地刚选出独立后执政党时那样。汽车,音乐,新衣服,当天的政坛英雄——你看得出来,因为他们抵达时群众格外兴奋。林地大饭店的露天舞台或剧场也张灯结彩,仿佛要举行嘉年华活动。
印度已经独立二十年了,却还有这种殖民时代的庆祝方式。在我初识南方的婆罗门文化之后,这又让我首度见到了南方的反抗:南方对北方的反抗,非婆罗门对婆罗门的反抗,黑色种族对白色种族的反抗,达罗毗荼人对雅利安人的反抗。这场反抗运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在一九六二年所接触到的婆罗门世界已经受到冲击。
一九六七年赢得邦选举的政党是“达罗毗荼进步联盟”(简称DMK)。这个政党有深远的根基,它有自己的先知及从政领袖,也就是在该党中相当于甘地和尼赫鲁的人物,而这些人的生涯也奇妙地跟印度主流独立运动领袖的生涯如出一辙。在那之前,我几乎未曾听人提过他们,也几乎完全不知道其运动的强大力量。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胜利,即表示不到五年前蜜糖带领我认识的那个文化——那个在我看来完整、神秘而古老的文化——已经溃败了。
蜜糖维持他素来的婆罗门作风,对发生的这些事满不在乎。他仍然住在迈拉波的父母亲家里,仍然到那间古老寺庙祭拜,仍然一副心满意足模样干着他一直干的公司文员职务。
时隔五年,他的友情依然殷切如昔。他还是像我所记得的那样忧郁,内心深处还在唠叨着什么。或许,他这时变得有点更加沉默寡言了。我想我们并没有谈到政治。在他父母亲家楼上的房间里,我们倒是谈到了几本他最近产生兴趣的泰米尔语预言书。他告诉我,这些是古老的书籍,现在邦政府将它们重印出版,一共好几册。
他说不出为什么会对预言书产生兴趣,不知道是因为想知道自己的未来,还是只是想读读那些书。这里有一份暧昧:他显然对那些书很着迷,但同时又似乎要我保持戒心,告诉我解读那些圣书的祭司常常要价很高。
他也读别的书。这些就在他房间里,他把它们拿了出来:英国的柔情浪漫小说,只是打发时间的——他这么说,仿佛书的内容对他并不重要,仿佛在他的孤寂中只要能够看书、有个消遣就好。
如今,二十多年后,我又来到马德拉斯。这一次,同样未出自刻意安排,我抵达时又正巧碰上政治活动期间。这里即将举行另一次邦级选举。各政党的广告牌、标志及政党领袖的画像到处可见。有些海报非常大,犹如马德拉斯的电影广告牌,这倒是恰如其分,因为自从原先的达罗毗荼政党分裂后,达罗毗荼运动所推出的领导人物就都是泰米尔电影明星。广告牌中所画的政治人物都有一副南方电影明星那种圆胖的脸形,甚至大家都知道是黑肤色的人也变得脸颊红润:领袖的画像应当如此。
在画像中,过去十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担任邦长的那位电影明星——由于他刚过世,才会有这次邦级选举——戴着一副墨镜和一顶白色皮毛小帽。无论从影或从政,墨镜和小帽是他不变的行头。他曾经是著名的特技演员,像是本地版的埃罗尔·弗林③,在影迷心目中,他几乎是个神。他比较感兴趣的是当一位统治者和明星,而不是处理政府事务。据说,他死的时候有一万八千件公文等着他批阅。他做过的事包括废除马德拉斯市政府,因此现在马德拉斯一团糟,到处垃圾堆积如山。仿佛这般情境——这种违背古老洁净观念的做法——也是南方反抗的一部分。
过去泰米尔纳德的殖民地抗争政治遵循了殖民地的发展模式:偷窃、耗损、停滞、言辞、古老悲情的不断撩拨。那些悲情倒不是虚构出来的。泰米尔纳德的人民尚未背离、摒弃原先的达罗毗荼抗争运动:这次选举对垒的一方是从DMK分裂出来的几个派系,另一方是剩下来的DMK本身。
一九六七年的赢家DMK这回又获胜了。在我抵达几天后,到处都是该党的黑红两色旗子——黑色代表种姓反抗,红色代表革命。在载客摩托三轮车上,在自行车上,这面旗子飘扬着,庆祝选战胜利。有时候,人们从小型客车打开的车窗伸出手去把旗子高举在车外,举起的手象征旭日的光芒,即选票上代表DMK的标记。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
相邻推荐:罗马爱经 少爷风流 命运的内核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队列之末:有的人没有 神的拉面 戏假成真:演瘾君子这么像?查他 列克星敦的幽灵 斯普特尼克恋人 玛格丽特小镇 魔山 死屋手记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队列之末3:挺身而立 队列之末4:最后一岗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 局外人 高塔[无限] 队列之末2:再无队列 茵梦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