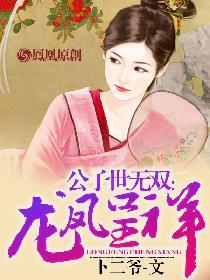龙腾小说网>印度三部曲3:百万叛变的今天 > 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1页)
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1页)
一九六二年,我对英国人留下的建筑大多未加特别留意。由于我在特立尼达已经和英国有过接触,印度的英国建筑在我看来似曾相识,不足为奇。或许也因为一九六二年印度刚刚独立了十五年,在那个年代,我只顾把英国建筑当作陪衬的背景看待。我向往的是印度过去的成就。甚至连新德里那几座鲁琴斯①的著名建筑我也不认为有什么特别可观之处,我觉得其规模过于炫技,我也在他的纪念性建筑中寻找他从莫卧儿建筑师承袭的主题,我在他的模仿修改里看到了更多夸耀的成分。
我甚至也用这种偏颇的眼光看待较不重要的英国建筑,包括在乡下为官员所盖的平房和别墅。这些屋舍住起来舒适,它们有柱廊和阳台、厚墙和高顶,有时窗户上方还有额外的窗子或开口,因此颇适合当地气候。但在印度贫穷乡间的衬托之下,它们显得太豪华。它们似乎还夸大了印度气候的恶劣程度。因此,虽然这些英国建筑完全属于印度,它们却仿佛把印度远远隔离在外。
但是,岁月飞逝,我们的感觉和观看方式也会随着变化。印度人已经在独立后的自由印度建设了四十年,他们在这段时间所建的东西令人更想看看之前的建筑。在自由印度,印度人像没有传统的民族那样建造,他们基本上是在呆板、肤浅地模仿国际风格。难以理解的是,印度人不像英国人那样,实际上不以印度气候为考虑。他们太执迷于模仿现代风格,大多数这样盖出来的房子——孟买那些单调乏味、方方正正又靠得太近的高楼,勒克瑙及马德拉斯的钢筋水泥怪物,新德里的住宅群落——只会使艰苦的热带生活更加艰苦,更加炎热难受。
自由印度的大多数建筑非但未能激发人们对美丽、雄伟和希望的欣赏——比起有钱人,陷于极度穷苦的人可能更需要这种振奋精神的情怀——它们反而助长了印度的丑陋、拥挤以及日渐严重的肉体煎熬。一个热带贫穷城市的恶劣建筑不仅涉及美感问题。它们糟蹋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磨耗人们的精神,引发了可能会四处流窜的怨怒。
比起任何殖民时代的英国建筑,这样的印度建筑都更加无视使用者的需要;因此,英治时代公共工程部所建的最简单实用的平房现在看起来像是考虑周全的建筑。如果从这里开始,再考虑印度境内英国建筑的诸多种类,其历时之长久,那两个世纪之中所呈现的不同风格,随时代完善的功能(火车站、加尔各答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孟买的印度门、勒克瑙及新德里的议会大厦),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英治印度的建筑——那么容易被视而不见的建筑——乃是这个次大陆上最好的非宗教建筑。
比起新德里,加尔各答更算得上是英国人建造的印度城市。它是英治印度的早期中心之一;它随着英国势力而发展,不断整修增建;直到一九三○年,它一直是英治印度的首府。加尔各答首先以宫殿之都著称,后来又成为大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建设加尔各答时,英国人信心满满,不以印度统治者所好的风格为本,而是把欧洲的古典风格移用到印度,借以标志外来文明的胜利。但是,经过两百年的发展,这个帝国城市也成为了一座印度城市,同时,作为一个港口,作为行政与商业、教育与文化、英国与印度时尚之中心,它也跟印度其他城市截然不同。一九六二年末,在经历了数月印度小镇及乡间生活之后,我一到加尔各答就立刻感觉到了大都会的气息:它有大都会的种种视觉刺激,在这里种种奇遇、利益和加强的体验都可能获得。
二十六年之后,这座英国人建造的城市的壮丽——宽阔的大道、广场、善加利用的河流和开放空间、妥善配置的宫殿和公共建筑——仍然可以在夜间像幽灵般被瞥见。此时,白天的人群已经回到他们的小窝休息,准备应付加尔各答另一个团团转、空茫茫、惨兮兮的日子:破损的马路和小径;汽油及煤油散发的褐色烟雾使得炽热的阳光更加凶猛,在皮肤上留下一层尘垢;世界上最破旧的大巴及汽车整日不停、此起彼伏、像蝉般尖叫的喇叭声。纵使只像幽灵,英国人建造的这个城市仍然看得见,因为自从独立以来几乎没有新的建筑。
精力和投资用到了别的地方。加尔各答没有得到眷顾,靠消耗自己的脏腑而生存,展示着一幅生命的假象。加尔各答市中心的某些建筑似乎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就未曾粉刷油漆过。在一些墙壁和柱子,例如待拆的建筑的墙柱上,旧海报和糨糊粘在一起,像干硬破碎的纸板。你设想着,如果要刮除那层东西,恐怕连水泥都会一起掉下来。著名的殖民时代俱乐部如孟加拉俱乐部、加尔各答俱乐部等正在衰败,印度人出入于过去不能涉足的场所。里里外外尽是衰败:加尔各答有几分像六十年代比利时人撤离后本地人擅自占领的非洲殖民聚落。擅自占领,情况就是如此。独立时,由于孟加拉被分割为属于印度的西孟加拉和属于巴基斯坦的东孟加拉,大批难民从东部涌入。他们哪里有地方就占据哪里居住下来,把城市内及周边好几大块地区都挤满了。从那时到现在,这座城市的人口已经增加了一倍。
白天,街道上或草木干枯的大公园里根本没有空间,没有可以散步的地方。你可以开车,非常缓慢地经过东挖西挖的马路和水泄不通的人群,前往托里衮吉俱乐部,在那里的高尔夫球场上散步。但是,这条路开得你筋疲力竭,然后,回程还得忍受的煤油汽油烟雾也会叫你败兴而归。别人会告诉你,直到十五年前,加尔各答市中心的街道每天都还会清洗。可是,我在一九六二年也听过同样的话。甚至在那时候,独立十五年之后,以及那几场会令许多人难忘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大暴动发生十六年之后,人们已开始怀念加尔各答的黄金时代。
英国人建造了加尔各答,留下了他们的标记。当英国人不再是统治者时,这城市也开始死亡,虽然这并非历史的必然。
齐达南达·达斯·古帕塔是一九六二年我在加尔各答见到的人之一。当时他在帝国烟草公司上班——这家公司后来改用不那么刺眼的简称ITC。因为他在这么一家显赫的英国公司工作,齐达南达是为数不多的人人称羡的被称为“提箱仔”的印度人之一。
这些提箱仔认为自己融合了印度和欧洲的文化。提箱仔的工作一方面跟英国人来往较多,乃是教养的象征,同时又稳定无虞,因此其他印度人对他们既钦佩又嫉妒。他们薪水很高,属于印度待遇最好的工薪阶层,另外——提箱仔在待遇上的锦上添花——公司还为他们提供汽车和备有家具的公寓。他们的职务并不繁重。提箱仔上班的每一家公司都或多或少独占了印度的某个领域。提箱仔必备的条件只是教养不错,关系良好,举止优雅。
齐达南达还有另一件事情做。他热爱电影,是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的创办人之一。有天晚上,我在加尔各答电影学会碰到了他。二十六年之后,有人——就是在孟买告诉我生平故事的那位秘书拉赞——提起这件事,说是当晚活动结束后齐达南达要他把我安全送回我住宿的制药公司招待所。我对拉赞毫无记忆,至于他,能够跟影坛人士及孟加拉上流社会在电影学会度过这样轻松的一夜可真是太棒了,让他稍微见识了远比他所知道的更加美好的加尔各答。我对学会的办公室只有很模糊的印象:塞满旧办公家具的小房间,天花板上一盏昏暗的灯。我记得齐达南达的提箱仔模样:四十岁,身材修长,蓄小胡子,穿灰色西装。
齐达南达没有在ITC待下去。他改行去拍电影和写作,这成了他的职业,也使他离开了加尔各答。大约二十年之后,他在半退休的状态下回到加尔各答。他半个礼拜的时间在《电讯报》主编文艺版,其他时间则住在圣蒂尼克坦——孟加拉诗人与守护圣人泰戈尔所创立的大学。
圣蒂尼克坦离加尔各答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车程。齐达南达正在那边盖一栋房子,先住在已经盖好的部分中,四周还在施工之中。我在一个星期天到那边见了他。
我设想这是由一个诗人兼教育家建立的类似甘地在南非所设立的凤凰村的机构:与独立运动有关联,同时又是反对过分制度化的产物。我知道这所学校有音乐课程、户外教学、茅屋教室:它有淳朴的田园风味,基础却很脆弱,靠着大家还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才得以存在,而且因为我很久未曾听人提过圣蒂尼克坦,我还以为它已经消失了。
我搭乘圣蒂尼克坦线快车前往,坐的是有冷气的休息车厢。车厢摆设得像起居室,有沙发和扶手椅。装潢的基调是佛教风味,车厢内一块围起来的地方过去可能还设有神坛:这令人想起,往北是佛教地区。我是这节休息车厢里唯一的乘客,加尔各答旅馆的领班为我付出的可怕票价终于有了解释。不过,我却一点都没有得到高级享受:铁路局的低层职员把休息车厢当作睡觉场所,眼前就有三个在沙发上打鼾大睡。
车外是三角洲上平坦无树、适合种水稻的土地,分别呈现绿褐两种颜色。绿色田里都是水,一畦一畦长着不同时期插种的稻子。在一些田里,尚未插种的成列的一捆捆秧苗立在水中,像小小的禾堆。已经收割的田地呈黄褐色,干涸无水,有些田留着稻梗,有些已经清理、犁过,有些田里隔着一段距离就有较黑的新土堆,等着犁进旧土以恢复地力。在许多地方,水从一畦田被引去另一畦,有时使用电力帮浦,有时用手将一种可移动的长筒降到有水的田里,再升起来把水倒入另一畦里。在这片宽敞的三角洲上可以看到每一种跟种稻有关的活动:沿途好几英里情况都是如此,实在很难理解这里会发生饥荒。但是,到了圣蒂尼克坦附近,土地开始变干,开始像是平坦的沙漠,有点令人生畏。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
相邻推荐:队列之末3:挺身而立 少爷风流 玛格丽特小镇 命运的内核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 局外人 队列之末2:再无队列 斯普特尼克恋人 队列之末:有的人没有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罗马爱经 死屋手记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茵梦湖 神的拉面 队列之末4:最后一岗 列克星敦的幽灵 高塔[无限] 戏假成真:演瘾君子这么像?查他 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