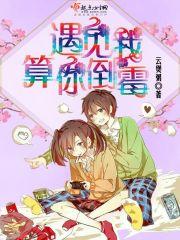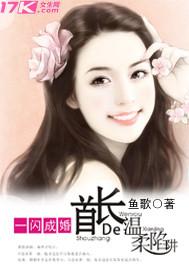龙腾小说网>漫长的余生 > 第21章 帝舅之尊(第1页)
第21章 帝舅之尊(第1页)
《魏书·灵征志》所列的“雾”,主要是大规模和严重的沙尘暴天气,如“雨土如雾”,“黄雾,雨土覆地”,“土雾四塞”,“黄雾蔽塞”等。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孝文帝太和十二年十二月,从丙戌日(489年1月28日)开始,连续六天“土雾竟天”,“勃勃如火烟,辛惨人鼻”。该志记北魏这类大雾凡九次,其中七次在宣武帝时期,并总结说:“时高肇以外戚见宠,兄弟受封,同汉之五侯也。”《魏书》把宣武帝时期沙尘暴天气频发归咎于高肇兄弟受宠,反映了北魏后期的一个主流,那就是对高肇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立场。《魏书》继承了这一立场。
高肇兄弟于景明二年(501)上半年被招入洛阳,骤然宠贵,大概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但高肇本人至迟已于景明三年秋被授予尚书右仆射的重要官职。《魏书·北海王详传》:“世宗讲武于邺,详与右仆射高肇、领军于劲留守京师。”宣武帝到邺城阅兵讲武,在景明三年(502)九月。那时高肇以尚书右仆射留守洛阳,高显以侍中陪同皇帝出行,兄弟二人兼顾内外,看起来是宣武帝特意的安排。高肇进一步高升,做到尚书令。《魏书》和《北史》都没有记高肇始任尚书令的时间,我推测在正始四年九月。高肇为尚书右仆射时,尚书令是广阳王元嘉。《魏书·世宗纪》载正始四年九月己未(507年9月24日)诏书,以“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司空”。元嘉腾出的尚书令位置,自然立即为高肇所占据,任命时间很可能在同一天或稍后。
高肇担任尚书令差不多四年半。《魏书·世宗纪》延昌元年正月丙辰(512年2月27日)“以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肇为司徒公”。延昌三年(514)冬以高肇为主帅统军征蜀,加大将军之号,仍居司徒之位,次年春回到洛阳被杀,司徒就是他的最终官职。《北史·外戚传》说高肇升司徒时,“虽贵登台鼎,犹以去要怏怏,众咸嗤笑之”。这时司徒最称荣耀,可高肇还是更看重把持行政实权的尚书令一职,这反映了他看重实际、专注于当下的风格,浸润于官场文化的那些人当然无法理解。
史书斥高肇恃宠专擅,核以记事,每虚多实少。《魏书·裴粲传》:“时仆射高肇以外戚之贵,势倾一时,朝士见者咸望尘拜谒。”朝士如此巴结(或畏惧)高肇,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不“望尘拜谒”,就会有麻烦呢?传文表彰裴粲,因为他就没有那么做,他见高肇时,只是按照常规礼节“长揖而已”。家人怪责,裴粲回答:“何可自同凡俗也。”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倒霉,高肇不曾给他穿小鞋。高肇当尚书令时,御史中尉是游肇,二人同名。高肇让游肇改名,游肇说自己的名字是孝文帝所赐,因此坚决不肯改名。《魏书·游肇传》:“高肇甚衔之,世宗嘉其刚梗。”虽然惹得高肇不高兴,却博得宣武帝赞赏,高肇也拿他没办法。高肇为司徒时,有个儒生刁冲因高肇“擅恣威权”而上表攻击他。《北史·刁冲传》记刁冲“抗表极言其事,辞旨恳直,文义忠愤,太傅清河王怿览而叹息”。很显然,刁冲也没有遭到高肇的打击报复。事实上,高肇的话宣武帝也不是都听。《魏书·良吏传》记宋世景特别能干,“台中疑事,右仆射高肇常以委之”,后高肇和尚书令元嘉一起推荐他做尚书右丞,因王显从中作梗,“故事寝不报”,宣武帝竟然没有批准。
见于史书的高肇主要罪状似乎都与几个亲王之死有关。北海王元详之废,《魏书·北海王详传》说是高肇诬告:“后为高肇所谮,云详与(茹)皓等谋为逆乱。”元详与茹皓勾结亲昵,已见前述,茹皓之败,牵连及于元详,而元详确有诸般劣迹。《魏书·彭城王传》把元勰遇难全都推给高肇:“尚书令高肇性既凶愎,贼害贤俊。又肇之兄女,入为夫人,顺皇后崩,世宗欲以为后,勰固执以为不可。肇于是屡谮勰于世宗,世宗不纳。”京兆王元愉反于冀州,元勰的舅舅潘僧固“见逼从之”,也就是说,潘僧固加入了元愉的叛乱。可是,潘僧固跟随元愉到冀州做官,恰恰是元勰推荐的。于是,传文称高肇诬告元勰“北与愉通,南招蛮贼”。元勰死后,其妻李妃号哭高叫:“高肇枉理杀人,天道有灵,汝还当恶死。”在宫里率领武士逼元勰喝下毒酒的元珍,据《北史·魏诸宗室传》,“曲事高肇,遂为帝宠昵”。宣武帝让自己宠昵的元珍动手处死元勰,恐怕不能说是高肇的主意。元愉在冀州称帝造反,据《北史·孝文六王传》,“称得清河王(元怿)密疏,云高肇谋为杀害主上”,兵败被俘,至野王“绝气而死”,“或云高肇令人杀之”。同传又说:“司空高肇以帝舅宠任,既擅威权,谋去良宗,屡谮(元)怿及(元)愉等,愉不胜其忿怒,遂举逆冀州。”这就把元愉造反的责任也推到高肇头上。元怿向宣武帝指控高肇,比之于王莽,提出“宜杜渐防萌,无相僭越”,“宣武笑而不应”。
史书有关高肇“贼害贤俊”“谋去良宗”的这几个事例,都与宣武朝权力斗争的核心问题有关,那就是宣武帝对几个叔父十分警惕。在一度威胁皇权的元禧、元详死后,宣武帝又担心皇叔元勰在背后支持几个皇弟,后来还的确出现了皇弟称帝造反的大案。在这几个亲王的不幸故事中,高肇当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与其说他是罪魁祸首,不如说他只是宣武帝用得称手的一个工具而已。这个道理,当时朝中诸贵,包括几个遭遇不幸的亲王,一定也都明白,只是不可点破。李妃见到元勰尸体,伤恸已极,愤怒已极,却也只敢咒骂高肇,其实她当然知道谁是真正拿主意的。
可以说,高肇代宣武帝担负起全部骂名,本是皇帝制度的内在要求。《魏书·任城王传》:“于时高肇当朝,猜忌贤戚。澄为肇间构,常恐不全,乃终日昏饮,以示荒败。所作诡越,时谓为狂。”元澄为孝文帝所亲用,名列六辅,元禧、元详亦颇为忌惮,宣武帝对他不可能不提防。元澄“常恐不全”,决不会仅仅因为高肇的“间构”。眼见元禧、元详、元愉、元勰如此下场,元澄采用自秽策略,“终日昏饮,以示荒败”。
当然,宣武帝最亲宠的高肇也是元澄不敢得罪的。《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传》记元澄子元顺事(元顺很可能是李令徽所生,李令徽的弟弟李子岳娶高琨之女,即高猛的姐妹,所以元顺和高肇是沾亲带故的):
时尚书令高肇,帝舅权重,天下人士,望尘拜伏。(元)顺曾怀刺诣肇门,门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贵客”,不肯为通。顺叱之曰:“任城王儿,可是贱也!”及见,直往登床,捧手抗礼,王公先达,莫不怪慑,而顺辞吐傲然,若无所睹。肇谓众宾曰:“此儿豪气尚尔,况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闻之,大怒,杖之数十。
元澄杖责元顺,可能是听说了高肇的那句评论。不过,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高肇还是有一定心胸的。元澄怕的不是高肇,而是高肇背后的宣武帝。不过宣武帝对高肇也不是盲目信用的。《魏书·乐志》记公孙崇为考定音律事于正始四年上表,以为金石音律所关至大,请求皇上派重臣主持,因为“自非懿望茂亲、雅量渊远、博识洽闻者,其孰能识其得失”。谁是这样的人呢?公孙崇表曰:“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度淹雅,神赏入微,徽赞大猷,声光海内,宜委之监就,以成皇代典谟之美。”这样神乎其神的美誉,高肇那时一定享受了很多,如今保留在史料里的已相当罕见。不过宣武帝不是糊涂蛋。《魏书·乐志》说“世宗知肇非才”,一方面同意公孙崇的表请,另一方面下诏“可令太常卿刘芳亦与主之”,找来一个真正的专家与高肇一起主持其事。
叙述与事实脱节是生活的常态,不过对于高肇,以及千千万万有幸被历史提到的人来说(虽然进入历史就意味着变形),更大的不公平和不真实发生在身后,在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中。试举一例。《魏书·天象志》有如下一条:
世宗景明元年四月壬辰,有大流星起轩辕左角,东南流,色黄赤,破为三段,状如连珠,相随至翼。左角,后宗也。占曰:“流星起轩辕,女主后宫多谗死者。”翼为天庭之羽仪,王室之蕃卫,彭城国焉。又占曰:“流星于翼,贵人有忧系。”是时,彭城王忠贤,且以懿亲辅政,借使世宗谅阴,恭己而修成王之业,则高祖之道庶几兴焉。而阿倚母族,纳高肇之谮,明年,彭城王竟废。
这一段叙述与分析的时间终点在景明元年(500)的“明年”,事件标志是“彭城王竟废”。如前所述,彭城王元勰“悲喜交深”地“释位归第”,在景明二年正月庚戌(501年2月18日)。那时高肇兄弟还在平城,未曾参与宣武帝从辅政诸王手中夺回权力的宫廷政变,与洛阳的权斗毫无干系,说宣武帝这时“阿倚母族,纳高肇之谮”,是一点也不符合真实历史的。事实上,正是在高肇担任尚书右仆射以后的景明四年(503)七月,被废的元勰才重新起用,高拜太师。上引这段对于星占的历史分析更违背史实的,是说“是时,彭城王忠贤,且以懿亲辅政”,似乎不知道元勰本来就不在六辅之列,说什么“借使世宗谅阴,恭己而修成王之业,则高祖之道庶几兴焉”,更是离题万里了。
身份制与等级制社会对出身与流动限度是非常敏感的,出身寒贱者只宜在一个限阈内流动,如果因某种机缘突破了制度设定的流动极限,进入由特定身份等级社会所专属的那个阶层,他就成为通常不受欢迎的特例。对高等级政治职务的垄断,反映了国家对高等级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制度性保障,与此相配合,就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设置,其基本舆论不仅是当时政治的晴雨表,也会反映在历史编纂中。突破身份的制度性极限,意味着必然面对否定性的社会舆论。清人钱大昕说:“六朝人重门第,故寒族而登要路者,率以恩倖目之。”目之为恩倖,就是对其权位予以伦理性的否定。
高肇家族既非拓跋崛起所赖的代人,又与华北名族的社会网络无关,骤得权势,超然于宗室及旧族之上,当然会被权贵社会视为异类,和那些被列入《恩倖传》的人物差不太多。《北史·外戚传》:“(高)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表面上是针对高肇的出身,其实是因为他过于突然地闯入了权势阶层。权势是限量供应的绝对奢侈品,在高等级社会内也存在着血与火的竞争,现在一个外人未经竞争而轻松攫取,可想而知,他必定成为整个高等级社会的眼中钉。
然而,皇帝制度又在法理上决定了一切政治权力都不过是皇权的延伸,也就是说,皇帝既是一切官爵合法性的来源,也是一切官爵的终极分配者。皇帝制度内在属性之一,就是皇帝可以突破已有制度。由此决定了官职竞争中总有弯道超车者,也总有火箭式干部。当宣武帝这样一个内心安全感甚弱,对外界难以信任的皇帝在位,他总是更容易信任那些与他有个人性联系的人。那么很自然的,他会信用当他还处在弱势地位时与他亲近的人,也就是东宫时期和亲政之前的侍卫、御医、宦官等等,再就是与他母亲有关联者,包括宫女和外戚。高肇兄弟“数日之间,富贵赫奕”,要放在这个背景下理解。
高肇以帝舅之尊,深得宣武帝信任,封以高爵,授以重官,只要这种信任不变,朝野内外是无人能奈他何的。但加官晋爵是一回事,操弄权柄是另一回事。有名有位,只是理论上有权有势,要实际上享受权势而不是被权势吞噬,还需要一定的个人条件或个人努力。《北史·外戚传》称高肇“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显然他具备一定的政务能力,而且他还喜欢做事。这样一个与既得利益集团全无联系的人,有政务才能又热衷政务的人,母舅之亲,把他放到尚书省长官的位置上,年轻的宣武帝就有了控制朝政的安全感。高肇虽一开始只是担任尚书右仆射,但尚书令元嘉“好饮酒,或沉醉”,不爱管事(或不敢管事),高肇实际上控制了朝廷政务。有了宣武帝的信任和支持,可以说高肇在官僚体系里不需要担心遭遇抗衡或威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高肇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肇并不是宣武帝最亲近的人。有人比他更靠近皇上,更懂得怎样与皇帝相处,也更得皇上信任,他们就是《恩倖传》重点写的赵修和茹皓等侍卫出身的亲信。跟他们比起来,高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够让宣武帝对他的信任保持长达十三四年,可以说始终不渝。而赵修、茹皓这样的亲信,固然一时亲宠无两,但他们都没有能力长期维持宣武帝对他们亲宠的热度。而且,当六辅消散,权势为宣武帝亲信人群所独享时,这个人群内部势必存在着权势分配的竞争。高肇能够成功上升,就因为他在所有竞争中都胜出了。当竞争对手一个一个被扳倒,高肇就成为宣武朝一个耀眼的政治现象。
据《魏书·恩倖传》载宣武帝黜落赵修的诏书,赵修最后的官职是散骑常侍、镇东将军、领扈左右,三者之中最有实际意义的是领扈左右。领扈左右,即领左右,是皇帝禁卫系统中最内层、靠近皇帝的卫士长(北魏末年的权臣如尔朱荣都要亲自兼任这个低级别武官)。赵修在东宫只是“白衣左右”,宣武帝即位后“仍充禁侍,爱遇日隆”,至迟在宣武帝亲政后就开始担任领左右了。宣武帝这封诏书写得十分讲究,显然是高聪、邢峦这一级别文士的作品。诏书为宣武帝开脱,说赵修“昔在东朝,选充台皂”,指赵修以白衣左右的身份服务于太子宫,在这个过程中与宣武帝建立起个人感情,所谓“幼所经见,长难遗之”。诏书以此解释为什么即位后不只要用他(“故纂业之初,仍引西禁”,东指太子宫,西指皇宫),而且还要重用他(“识早念生,遂升名级”),尽管他是不值得重用的(“地微器陋,非所宜采”)。
赵修的高光时刻并不长,延续了不到两年。他在宣武朝所做的事情中,长期政治影响最大的,是说服宣武帝立于劲的女儿为皇后。据《魏书·世宗纪》,景明二年九月己亥(501年10月5日),即处死元禧三个多月后,“立皇后于氏”。《北史·后妃传》记宣武顺皇后于氏:“以嫔御未备,因左右讽喻,称后有容德,帝乃迎入为贵人,时年十四,甚见宠爱,立为皇后。”这个能对宣武帝施加影响的“左右”,就是赵修。于劲是领军将军于烈之弟,于劲应该与其家多人一样,都在禁军任职。他们在宣武帝夺权和挫败元禧谋反的斗争中立下大功,因而也与宣武帝身边的亲信侍卫建立了私人联系。
《魏书·恩倖传》:“初,于后之入,(赵)修之力也。”一年多后赵修被捕时,他正在于劲家玩游戏(樗蒲),尽管可能是于劲受命为稳住他而特意招他来玩(如此怀疑是因为赵修被捕后带到领军府受审),于劲和赵修关系亲密是无疑的。《魏书·恩倖传》:“(赵)修死后,领军于劲犹追感旧意,经恤其家,自余朝士昔相宗承者,悉弃绝之,示己之疏远焉。”史书不记于劲为领军的时间,我猜可能在景明三年八月。《魏书·于烈传》:“顺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弥见优礼。八月,暴疾卒,时年六十五。”于烈死后,于劲继为领军。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
相邻推荐:涟漪效应时星草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笔趣阁 人家是一头好人[末世]萨巫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笔趣阁 漂亮小狐狸被迫修罗场[无限] 咒灵操使,但小学生 美食评论家 古代小清新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笔趣阁 最佳位置吴少贵生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笔趣阁 嫁给兄长的竹马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笔趣阁 五灵神卫 盘龙之史上最强 权色巅峰 我只想安静地当个魔法师 冷艳校花华丽归来 嫁给一座荒芜城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笔趣阁 偷吻时星草笔趣阁无防盗章 末世第十年扶华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笔趣阁 末日浩劫:情与恨难抉 穿进权谋文后绑定了农场系统 偷吻时星草原著小说未删减版 火影之水白赖